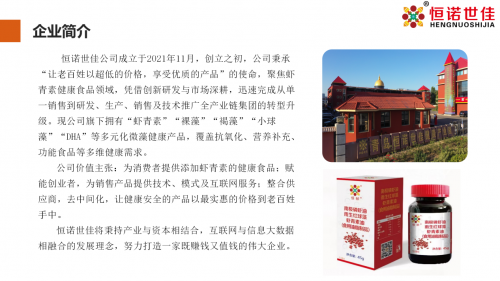产权界定滞后: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现实梗阻
数据要素的特殊性在于其非稀缺性、虚拟性、非耗竭性、非排他性与可复制性,这使得其产权界定远比传统生产要素复杂。2022年出台的《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(即“数据二十条”)首次提出数据资源持有权、数据加工使用权、数据产品经营权“三权分置”的制度设计,为数据流通提供了初步规则。但该框架回避了最核心的所有权问题,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呈现“源头模糊、中游混乱、下游失衡”的结构性矛盾。
个人数据作为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的“源头活水”,其所有权归属是整个数据产权体系的逻辑起点。大量公共数据来源于个人行为记录(如水电缴费、交通出行等),企业数据中用户生成内容(UGC)占比也较高。这些数据在收集过程中,往往通过“格式条款”被平台无偿占有——用户点击“同意”按钮的瞬间,便丧失了对自身数据的控制权。一些互联网平台的用户协议中明确规定:“用户同意将所有数据永久、免费、不可撤销地授权给平台使用”,这种不平等的权利让渡,形成了数据要素分配中的强者更强弱者越弱的“马太效应”。个人数据收益占比与数据生产者的贡献严重不匹配。
公共数据领域的产权模糊问题更为突出。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管理、公共服务等途径收集的海量数据,其所有权归属长期缺乏法律界定。有的地方交通部门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智慧停车系统,基于市民出行数据产生收益,但数据贡献者未获得任何分成;有的省级电力公司利用用户用电数据构建负荷预测模型,被第三方企业收购,而众多用户对此毫不知情。这种“数据采集免费化、数据应用商业化、收益分配垄断化”的模式,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,更抑制了公众参与数字经济的积极性。不少受访者因担心数据被滥用而拒绝提供非必要信息。当衡阳18亿拍卖政务数据、重庆市涪陵区1.08亿转让数字资产等重磅消息闯入公众视野时,却都无一例外遭遇迅速叫停的命运,宛如一记记重锤,敲打着数据产权敏感的神经,也引发了无数疑问与沉思。叫停主要因素就是数据产权不明晰,假若公共数据中明确哪些数据归政府所有,哪些数据归企业所有,哪些数据归个人所有。合法确定数据所有权,取得的收入根据所有权返给数据贡献者。正如笔者采访某政府分管副市长时他说:很多地方政府财政十分紧张,却守着大量值钱的公共数据不敢变现,主要原因就是数据产权不清。导致数据供给的“自愿性短缺”。
企业数据的产权边界同样存在争议。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对个人数据进行加工形成的数据产品,其权利性质如何界定?曾有电商平台与数据服务商的侵权纠纷,法院虽认定服务商非法爬取数据构成侵权,但未明确平台对这些数据的权利基础。这种司法实践中的模糊性,使得企业不敢投入巨资进行数据开发,很多企业因顾虑产权保护不足而不愿开放核心数据参与跨行业流通。
产权不明晰导致的“公地悲剧”正在显现:一方面,数据持有者因缺乏排他性权利而不愿投入资源进行质量提升;另一方面,数据使用者因权利无保障而不敢深度开发应用。这种“双输”局面直接制约了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,我国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和价值转化率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。破解这一困局,亟需从法律层面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属,构建“归属清晰、权责明确、保护严格、流转顺畅”的现代数据产权制度。
科斯定理的启示:产权明晰如何激活数据要素价值
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·科斯在《社会成本问题》中提出的核心观点,为破解数据产权困境提供了理论钥匙。科斯定理的核心要义包括两点:其一,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,无论初始产权如何分配,市场机制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;其二,当交易成本为正时,初始产权的清晰界定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。这一理论揭示了一个朴素真理: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,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,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,资源配置必然陷入低效。
数据要素的特殊属性使得其交易成本远高于传统要素:数据的无形性导致确权成本高,可复制性增加了侵权风险,时效性要求加快了交易节奏。这些特性使得数据市场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,此时初始产权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关键。如果个人数据所有权归属模糊,数据收集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便无法厘清,必然导致要么过度保护阻碍流通,要么保护不足引发滥用。只有明确个人对其数据的所有权,才能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数据价格,实现“谁贡献、谁受益”的良性循环。
数据产权明晰不仅是激活数据要素市场的关键,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。一旦个人数据产权明晰,就如同1978年农村改革“土地承包到户”一样,将极大地激活广大群众参与数字经济的热情。当民众真正掌握了数据的主动权,他们将积极在依法依规保护隐私权的前提下,让个人数据、家庭数据和企业数据参与交易,从而为自身、家庭和企业创造财富 。这种模式将促使数据要素在更广泛的群体中流通共享,缩小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,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。民众通过贡献数据获得收入,不仅增加了自身的经济收益,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,形成“供得出、流得动、用得好、保安全、惠民生”的全民参与、共享数字经济红利的良好局面。
巴西在个人数据产权市场化方面的实践,为科斯定理的应用提供了生动注脚。2020年《巴西通用数据保护法》(LGPD)实施后,该国创新性地推出“个人数据钱包”制度:公民通过政府认证的数字钱包管理个人数据,企业使用数据需支付报酬,用户可自主选择数据使用范围和价格。这种模式的成功,正是源于明确的初始产权界定——法律明确个人对数据享有所有权,企业使用必须获得授权并支付对价,由此降低了数据交易中的协商成本和侵权风险。
巴西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:数据产权制度设计必须立足国情,在保护个人权益与促进数据流通之间找到平衡。与巴西相比,我国具备三大优势:一是制度优势,能够通过顶层设计统筹数据安全与发展;二是规模优势,庞大的网民数量形成超大规模数据市场,可通过网络效应降低交易成本;三是技术优势,区块链、隐私计算等技术为数据确权、溯源提供了技术支撑。这些优势意味着,我国若能构建科学的个人数据产权制度,完全可能实现更高的效率与公平。
从科斯定理视角看,个人数据所有权的明确界定将产生三重效应:其一,激励效应,公众因能获得数据收益而更愿意提供高质量数据,解决数据供给不足问题;其二,约束效应,企业需支付数据使用成本,倒逼其提高数据利用效率;其三,协同效应,清晰的产权降低了交易成本,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流通融合。这三重效应共同作用,将推动数据要素从“无序占有”向“有序流通”转变,从“垄断收益”向“共享增值”转型,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。
数实融合的枢纽:产权明晰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
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,而数实融合正是连接两者的关键纽带。数据要素只有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,才能真正发挥“乘数效应”。但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,必须以清晰的产权为前提——没有产权保护,企业不敢投入数据应用;没有收益预期,公众不愿参与数据共享;没有流通规则,跨行业数据融合无从谈起。数据产权制度如同数实融合的“交通规则”,只有规则明确,数据要素才能在实体经济的“高速公路”上高效通行。
在制造业领域,产权明晰推动数据成为生产过程的“神经中枢”。有的汽车制造商在明确用户驾驶数据所有权后,通过与车主签订授权协议,获得了大量车辆的实时运行数据。基于这些数据,企业对发动机参数进行了多项优化,提升了燃油效率,节约了成本。同时,车主因授权数据使用获得收益分成,形成“企业降本、用户获益”的双赢格局。这个案例印证了一个规律:当数据产权明确后,制造业企业可以更放心地推进数字化转型,通过数据反馈持续优化生产流程,实现从“经验驱动”向“数据驱动”的转变。产权制度完善的行业,智能制造普及率和生产效率相对更高。
农业领域的数据产权创新,正在重塑传统生产模式。山东某农业合作社探索“数据入股”模式:农户将土地墒情、作物生长等数据授权给农业科技公司使用,公司支付数据报酬,同时将数据分析结果反馈给农户指导生产。实施后,该地区小麦亩产提高,农药使用量减少。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,通过明确农户的数据所有权,解决了农业数据“收集难、质量低、应用少”的问题。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开展类似试点,带动参与农户增收,提升了数据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。
服务业的数据产权改革,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。在医疗健康领域,有的互联网医院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个人健康数据确权平台,患者可授权医院使用其病历数据进行科研,科研成果转化后按比例获得收益。这种模式下,医院获得了高质量的研究数据,患者分享了数据价值,推动了新药研发,参与患者也获得了收益。在金融领域,明确个人信用数据所有权后,有的消费金融公司通过付费获取用户授权数据,降低了坏账率,用户也获得了信用数据收益。这些案例表明,产权明晰能够打破服务业的数据壁垒,促进数据在不同主体间有序流动,催生出更高效、更普惠的服务模式。
数据产权明晰对区域协调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。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资源分布极不均衡,东部地区拥有较多的数据中心和算力资源,但中西部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特色产业数据。通过建立跨区域数据产权交易机制,可实现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。“东数西算”数据产权试点中,有的西部省份将当地旅游数据授权给东部企业开发,获得了数据收益,还带动了旅游收入增长,这种“数据飞地”模式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路径。
数实融合的深度与广度,最终取决于数据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。当数据所有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的边界清晰后,数据要素才能真正成为激活实体经济的“催化剂”,推动产业结构升级、生产效率提升、民生福祉改善。建立完善的数据产权制度,将提升数据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,带动数字经济规模扩大。
从农业经济的土地产权确立,到工业经济的知识产权保护,每一次生产要素的产权革命都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。在数字经济时代,数据产权制度的构建将成为新一轮生产力解放的关键。当前,我国正处于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关键期,唯有抓住产权明晰这一“牛鼻子”工程,才能破解数据流通的制度障碍,释放数据要素的磅礴动能。
推动数据产权明晰,需要构建“法律保障、技术支撑、市场运作”三位一体的体系:在法律层面,加快制定“数据产权法”,明确个人数、企业数据、公共数据所有权的边界;在技术层面,运用区块链、隐私计算等技术建立数据确权、溯源、交易的技术支撑体系;在市场层面,培育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市场,形成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。通过这三方面的协同发力,让数据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“资产”,让老百姓在数据共享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,让企业在数据应用中提升创新能力,让国家在数据流通中增强综合国力。
高质量发展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获得感、每一家企业的创新力、每一个行业的竞争力之中。当数据能够获得合理回报,当企业数据能够安全流通,当公共数据能够高效利用,数据要素就能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“新引擎”,推动我国经济在数字时代实现质的飞跃,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。这场数据产权革命,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,更是我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。